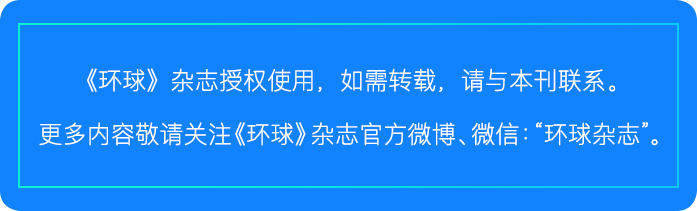在苏丹,何以为家

7月13日,在苏丹加达里夫的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流离失所者领取慈善机构提供的衣物
文/《环球》杂志记者 张猛(发自开罗)
编辑/马琼
2023年4月15日,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发生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并延宕至今。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数据,冲突导致苏丹1000万人流离失所。
然而,无论身处国内,还是在逃难途中,抑或是逃至邻国,他们始终难以摆脱重重困境。苏丹民众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回不去的家乡。
“如果能回到战前,少活两年都行”
在喀土穆西部恩图曼市一间狭小、潮湿、昏暗的房间内,62岁的穆塔瓦基勒·沙班眼神黯淡,身形消瘦。去年4月29日晚,一伙自称快速支援部队的武装人员突然闯入他家,强行将他们赶出去。一夜之间,沙班一家成了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苦难自此开始。
“我因刚做完手术,只能待在家中。我向士兵们苦苦哀求,但他们不管不顾,还用枪托打我的头。”沙班说,他们就是一群土匪,甚至连一件衣服也不允许带走。就这样,沙班一家当晚被迫离开恩图曼市中心的阿布鲁夫区,内心满是不舍、恐惧和屈辱,不知何时能再返回。
沙班脊柱受损,无法远距离迁徙,靠着驴车从阿布鲁夫区行至恩图曼最北端已是极限。他的妻子和3个女儿只得就近把他安置在一座清真寺旁的一个破旧小屋,然后分别逃往苏丹中部森纳尔州和埃及避难。
沙班落脚的地方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家。铁皮围成的房间低矮闷热,屋内除了两张床,以及床边放着的一个水壶和小风扇,再没有其他像样的陈设。身有残疾的沙班大多时间都半躺在床上,既得不到医疗服务,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所幸慈善组织的几名青年志愿者不时照看,才不至于饿死。
比起饥饿、病痛,让沙班最难以忍受的,是妻离子散的孤独感。因通信和互联网中断,沙班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络。“我很担心家人,想她们了,就看看手机里的照片,总是看着看着就哭了。”沙班说话时努力控制住情绪,但双眼再度湿润。
提到家与家人,沙班的嘴唇开始颤动,“如果能回到战前的生活,哪怕让我少活两年都行”。曾在印刷和出版机构工作的沙班喜欢阅读,孤苦伶仃的日子里,志愿者们带来的《向北迁徙的季节》等小说,成了陪伴他的“好朋友”。
持续冲突迫使大量像沙班这样的苏丹民众逃离家园。多个联合国机构警告:苏丹面临着世界最大的难民危机。留下的人身心备受折磨,而有些人虽然逃到国外,苦难也远未结束。
“一些孩子的画总是与武器、尸体和废墟有关”
去年11月,冲突蔓延至苏丹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市,城内枪声和尖叫声此起彼伏,到处弥漫着死亡气息。穆罕默德·雅各卜·伊斯梅尔一家十分害怕,不得已加入到徒步乍得边境城市阿德雷的逃难队伍中。因为匆忙上路,什么行李都没有带。
从朱奈纳到阿德雷的直线距离约为28公里,需要穿过大片沙漠,更大的危险是,西达尔富尔州的部落武装团体在该州边界不时向人群射击。伊斯梅尔说,“这次逃亡真的是九死一生”。短短20多公里路程,48岁的伊斯梅尔带着妻子和5个孩子走了5天,而与他们同行的数百人,有不少永远倒在了途中。
“我的一个亲戚背部中弹,因失血过多而死。”伊斯梅尔一家顾不上伤心、口渴和饥饿,白天几乎不敢停下歇息。他的小女儿在路上发起高烧,身体不停地抽搐。伊斯梅尔说,“我们没有药,只能用湿布帮她降温,当时我真担心她撑不过去”。
跨过苏丹边境线的那一刻,伊斯梅尔潸然泪下,回头望向祖国,不知该为全家死里逃生而庆幸,还是为变成难民而难过。
“我们为什么要住在帐篷里?我想回家。”在乍得边境一侧的苏丹难民营,面对小女儿隔三差五的询问,伊斯梅尔无法解释,只能回答“快了,快了”。
南苏丹首都朱巴以西25公里处的戈罗姆难民营里生活着上万名苏丹难民。苏丹冲突爆发后,赛义夫丁·易卜拉欣一家六口从喀土穆辗转多地,历尽艰辛逃到这里。“我只想给家人找个安全的地方,远离战火。”易卜拉欣说。
43岁的易卜拉欣原本在一所小学教美术,妻子是一名会计,家里有车有房,生活虽谈不上富足,却也其乐融融。如今,一家人挤在一个破帐篷里,冬冷夏热,雨下大点儿还会漏水。“没有工作收入,仅靠难民营救济,我们很难填饱肚子。”
尽管如此,当易卜拉欣发现难民营里许多孩子不仅瘦骨嶙峋,还受到恐惧和梦魇折磨,便决定每周抽出两天时间,教孩子们绘画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在授课初期,一些孩子画的内容总是与武器、尸体和废墟有关。”易卜拉欣鼓励孩子们用画笔释放心中积压的负能量,找回失去的童真。
“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健康成长,接受学校教育。如果苏丹的战火停止,我和家人会立即回去。”易卜拉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