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在乌镇:叩问当下,撞击人心

《海边》剧照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
编辑/黄红华
每年,受邀来到乌镇戏剧节的世界戏剧大师都是光芒最盛者。今年来到乌镇的戏剧大师尤其多,尤金尼奥·巴尔巴、铃木忠志、克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瓦日迪·穆瓦德……在他们的作品表达中,在“小镇对话”中,在采访中,《环球》杂志记者一步步走近他们,感知他们对创作的理解和对生命的哲思。
今年乌镇戏剧节开启了它的第二个10年,主题也由此前的单字变成了双字——如磐。在戏剧的长河里,这些大师就像一块块磐石,坚定地立在自己的位置上,展现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美学风格。他们风格不同、审美不同、理念不同,但都拥有叩问当下的使命和撞击人心的力量。
巴尔巴:记录现实中所发生的事
观众被收走手机后,被导演带进一个小小的黑匣子表演空间,大家自觉挤得更紧凑些以便让更多场外排队的人能够进来。演出过程中观众实现了近乎绝对的专注,没有剧场常见的手机“咣当”掉落地板的声音,演出结束后没有谢幕,没有拍照。这就是丹麦戏剧大师尤金尼奥·巴尔巴和他的欧丁剧团带来的极具仪式感的作品《哈姆雷特的云》。
哈姆雷特的故事一遍遍被演绎,巴尔巴的哈姆雷特又是什么样子?他将先后经历丧子与丧父之痛继而创作出《哈姆雷特》的剧作家与剧中人放在同一舞台上,由一名年长女性演员扮演莎士比亚,演出如同一场古老仪式。他对每个角色的悲剧命运给予关怀,包括通常被认为是反派的哈姆雷特的母亲乔特鲁德——当哈姆雷特悲伤地抱着死去的奥菲利亚,乔特鲁德也悲伤地抱着死去的弑兄娶嫂者克劳狄斯。现场放映的影像中还加入了当今世界饱受战争之苦的儿童,巴尔巴把对他们的怜悯与对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之子的怜悯融合在一起。很多观众看到影像中无助的加沙儿童时,都不禁流下泪水。

《哈姆雷特的云》剧照
巴尔巴60年前创立了欧丁剧团,今年已88岁高龄的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今年是他第四次来到乌镇,作为乌镇戏剧节发展的一名见证者,他称自己在乌镇找到一种“教父”的感觉。
《环球》杂志记者上次在乌镇见到巴尔巴是在2019年。这次再见,他依然精神矍铄,依然亲自将观众一一引入剧场。他把剧场当作自家客厅,观众来看演出就是到他家里做客。今年他带来的两部作品《舞者的一天》和《哈姆雷特的云》,依然在关注外界变化和个体命运。《舞者的一天》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讲一个普通人在理想与现实之前的徘徊;《哈姆雷特的云》提出的问题,不只是向内的“生存还是毁灭”,还有向外的“世界为何这样”。巴尔巴说,“今天,这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大部分人都无法去记录这些变化及其后果。”欧丁剧团在舞台上呈现的,就是记录现实中发生的事。
巴尔巴被称为“戏剧人类学的开拓者”。他认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表演者有自身独特的风格形式,但在表演上遵循一种共同的原则。欧丁剧团的演员来自世界各地,中国青年戏剧导演丁一滕曾前往欧丁剧团学习交流,学成归国后,他独创了融合中国古典戏曲与西方当代戏剧的“新程式”戏剧,成为中国青年戏剧创作者中的标杆人物。
巴尔巴特别在意其作品与观众的连接。他要求观众不带手机入场,是因为这样可以让所有人更专注、不被打扰,演出结束后观众是鼓掌而非拍照。他让观众分坐两侧,演员在中间窄窄的过道表演,观演双方融合极深。
但他并不指望作品会改变观众的想法,只希望能够给他们启发与感动,“我的观众包括儿童和聋哑人,盲人和学者,宗教信徒和无神论者,相信鬼魂存在的人和嘲笑这种迷信的人。我试着忘记自己的知识和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知所信不再引导我。”
铃木忠志:为欧里庇得斯的远大眼光而震惊
85岁的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也是乌镇戏剧节的老朋友,今年他带来了自己的经典作品《酒神》。他将古希腊戏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酒神的女信徒》以“铃木训练法”的表演形式呈现在舞台上。
铃木忠志将日本能剧、歌舞伎和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相结合,创造了独特的“铃木训练法”,被传授到世界各地的学校和剧院。“铃木训练法”要求演员强化对身体的控制,使演员在静的状态下蕴含巨大能量。铃木忠志坚持不让演员戴麦克风,而用中气将声音传达至后排观众。
剧中,酒神狄俄尼索斯为了惩罚不信奉他的底比斯王彭透斯,迷惑他的信众——包括彭透斯的母亲阿高埃在内的底比斯女人的灵魂,诱使她们杀死彭透斯。神志不清的阿高埃提着彭透斯的头颅回到城中,清醒后发现儿子被自己亲手杀死,对待这一场戏,演员不是泪如雨下的哭诉和歇斯底里的哀嚎,而是长时间里保持一片死寂,但那被压抑的愤怒、绝望与悔恨不亚于火山般爆发,并化作生命尽头的一声嘶吼。这就是“铃木训练法”的生动诠释。

《酒神》剧照
酒神狄俄尼索斯被称为“戏剧之神”。古希腊人在葡萄丰收的季节祭祀酒神,他们由唱歌跳舞逐渐发展成演绎故事,戏剧由此诞生。在铃木忠志看来,酒神是暴力之神,也是和平之神,“酒神让人忘记自己的痛苦,让人更幸福、更平静。《酒神》是一部关于文化摩擦和冲突的巨作,我今天仍会为古人欧里庇得斯的远大眼光而震惊。”
瓦里科夫斯基:分享苦难,得到治愈
波兰戏剧通常与严肃、深沉、激进、直面、残酷等关键词相关联,克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就是其典型代表。瓦里科夫斯基作为当代欧洲顶尖的前卫戏剧导演之一,擅长用直接、粗粝、华丽的方式进行舞台呈现,去探讨历史记忆、身份认同、社会思考等议题,以戏剧为刃揭开波兰曾被入侵的历史与伤痛。
今年的乌镇戏剧节,瓦里科夫斯基带来了开幕大戏《我们走吧》,它改编自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的《旅人》。3个多小时的时长,呈现了一方由5个家庭组成的社区、25个角色以及8场葬礼。社区里的家庭各自过着乏味的生活,他们想逃离却一次次被庸常生活囚禁:安茨亚出走美国又回来;成天说要去瑞士的艾勒哈南,再三将积攒的旅费花在与妓女的欢愉上;从疗养院屡次出逃的老妇伯芭,不断被儿子送上回疗养院的车……众人在“离开和回归”的循环中机械重复着,最终倒在了出逃之路上,死亡也是一种离开。
对于《我们走吧》所探讨的生命本质与死亡议题,瓦里科夫斯基说,他希望死亡不是简单的“就是死了、结束了”,不是一个破坏性的结局,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他想要重新开启一些东西。“在这部剧的结尾,我希望大家并不是真的死亡,而是就像在天堂电影院里、在梦里、在想象中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因此,结尾处,艾勒哈南一家三口坐成一排,开心地吃着冰淇淋,“就像在天堂电影院里看电影”。
瓦里科夫斯基表示,之所以选择诠释《旅人》这部作品,是因为里面有列文经常探讨的母亲、家庭、社会议题。他认为,社区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中被削弱了,“我们离开了我们出生的那个所谓的社区,逐渐变得孤独。我们的社区在哪里?”

《我们走吧》剧照
在瓦里科夫斯基看来,剧团就是他的社区,“我选择做戏剧,是因为想保持一个自由的状态。我从现实逃出来,进入了戏剧世界。我们的剧团就像一个独立于外界社会的乌托邦般的社区,但我们可以通过自由创作与外界进行沟通和对话。”
对于瓦里科夫斯基来说,戏剧创作源于生活中的苦难,但它的喜悦之处在于可以与一群非常亲密的人在一起,真诚分享每个独立个体的苦难或有阴影的过去。“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跟任何人分享其一生的苦难、阴影和过去。对于我来说,这是毁掉我们的一种毒素,而戏剧可以帮我们把这种毒素排出来。通过分享,得到治愈。”
穆瓦德:讲述上一代人未曾传达的真相
开幕大戏《我们走吧》是讲“离开”,闭幕大戏《海边》主题是“回归”。
瓦日迪·穆瓦德出生于黎巴嫩,在内战期间随家人逃亡至法国,后来定居加拿大魁北克省,现在担任法国柯林国家剧院总监。穆瓦德总是在自己的剧作中反思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巨大创伤,同时他对年轻人投以更多观照。
由他编剧、导演的《海边》讲述的是,一个迷茫的年轻人威尔弗里德为安葬父亲而去往父亲的故乡,却只看到战争之后的满目疮痍,找不到一处能够埋葬死者的地点,只得继续前行,更多年轻人与威尔弗里德结伴踏上旅途,每个人都将威尔弗里德的父亲当作失去的亲人的象征,这些年轻人决意带着战争的创痛继续生活,让属于自己的鲜活记忆为更多人知晓。
穆瓦德将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诗金融入《海边》,这三个著名的文学作品人物,一个杀了自己的父亲,一个决心为父亲复仇,一个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穆瓦德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另一部作品《焦土之城》,加拿大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曾将其改编成电影,这部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讲述的也是一个俄狄浦斯式的悲剧。
对于“悲剧的永恒性”,穆瓦德向记者阐述了他的观点,“个体在自我认知(你以为自己是谁)与自我身份(你是谁)之间存在着一段距离,这种距离才是人类悲剧的核心。古希腊悲剧正是通过这种探索去揭示人性的复杂,俄狄浦斯就代表了这种无知的状态,他以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但最终得知真相,继而失明,这种不可预知的触摸真相的速度是他未曾预料到的。索福克勒斯认为,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真相本身,而在于我们接近真相的速度。”
穆瓦德常向长辈们询问黎巴嫩内战的真相,但得到的回应却总是模糊或者避重就轻。他发现,上一代人刻意抹去内战的某些记忆,使得这些痛苦的历史没有被妥善传承。他感到有责任去探究和揭示这段历史,通过戏剧,既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试图讲述上一代人未曾传达的真相。
当记者问穆瓦德,对战争、历史、记忆、身份认同等议题有没有通过戏剧创作获得答案,穆瓦德回答,“我很无力,我没获得任何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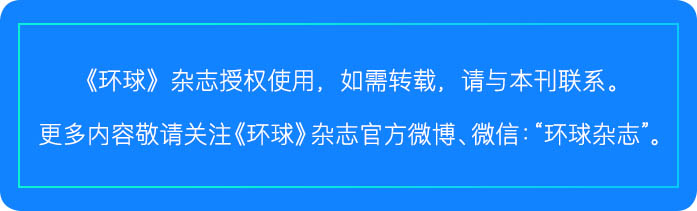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