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坛冬之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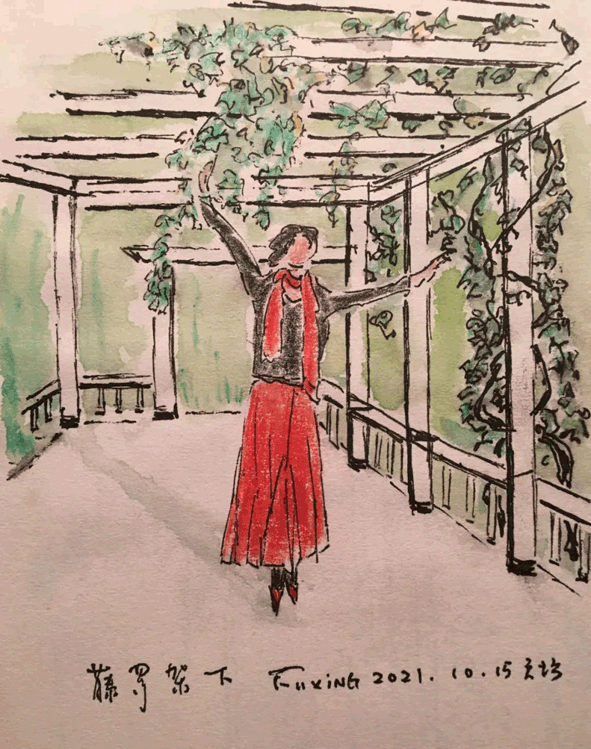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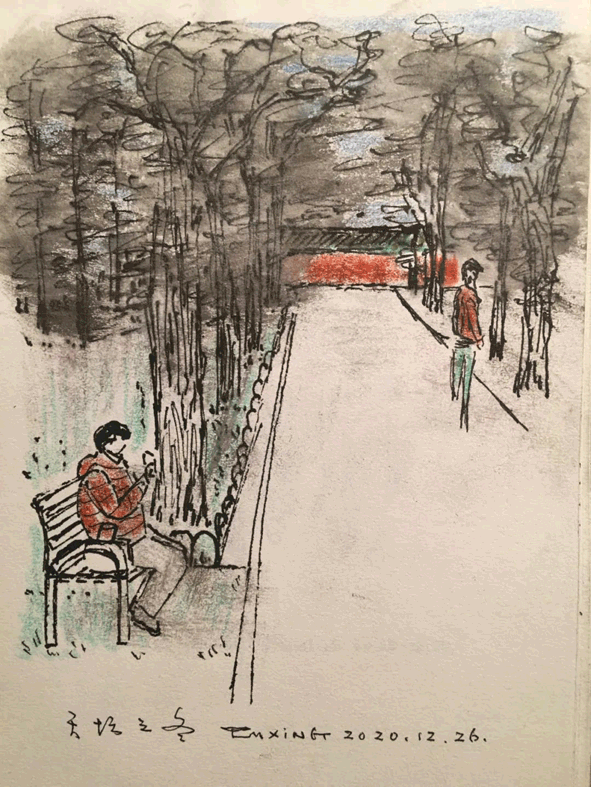
肖复兴
双环亭:初雪后的舞蹈
今年冷得早,11月初就落了初雪,非常大,风刮得也猛。明知道天坛的银杏叶子要被吹落了,还是忍不住去看看。没有想到,银杏叶竟然落得干干净净,片甲不留,枯枯的树枝裸露着树皮,和土拨鼠的颜色一样,灰褐色,有些黯淡,没有了风中金黄叶子的明亮。想起去年这个时候,银杏树摇曳着一片碎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简直有些像梦一般不真实。大自然真的是厉害,雕塑师一样恣意雕塑着树的样子,甚至改变整个世界的样子。
不仅银杏树的叶子落光,桃李、丁香、槐树、西府海棠、龙爪槐、柿子树,还有藤萝的叶子都落光了,只有松柏依旧绿荫森森。这就看出了天坛的厉害,它的松柏多,那些落叶树便被淹没在这样松柏的海洋里了。这时候以至整个冬天的天坛,绿色依然是它的主色调。
从东门走到北门,走过花甲门和百花亭,一直走到双环亭前,看见亭中有几个女人在跳舞。年龄不小,身穿的毛衣鲜艳,宛若春花烂漫。她们嘴上喊着“一二三”的节拍,一对对伸展着手臂次第向前跳过来,再向两旁退去,然后循环往复,好像花瓣渐渐绽开,鲜艳的毛衣起到了作用,暂时遮掩住了白发和皱纹的沧桑,好像春回二度。
我向她们走了过去,一位女人朝我说:你来帮我们录段像好吗?我说没问题。她从包里拿出手机,跳下亭子的台阶递给我。录了两次,看到了两遍春花绽放。她又对我说:你再帮我们照张合影吧。说着,招呼着伙伴跳下台阶,对我说:把双环亭照全,难得我们合影。
看清了,一共6个人。问清了,是社区舞蹈队的,年龄最大70多,最小的60多,属于佘太君祖母级的舞蹈队。还问清了,舞蹈是自己编排的,其中年龄最大的老大姐是她们的导演。
你们今天怎么到这里排练了?我问。她们告诉我,今天是来拍抖音,双环亭这里景色好。我们正等着谁能帮我们拍呢,这不您就来了!
我对她们说:选这个地方好!双环亭是乾隆皇帝为他母亲祝寿而建的,也是祝福你们长寿呢!
她们呵呵笑了起来。
心情、风景、祝福的话,三位一体——尽管只是过年话,也是舞蹈尤其是老年舞蹈必不可少的伴奏。
古柏树林:梵音鼓
丁香树丛前,是一片古柏树林,听见一阵音乐从那里传来,声音不大,却不绝如缕,像是寺庙那种袅袅的磬音禅乐,回音清新缥缈。走过去一看,一对中年男女,男人坐在长椅上,双手拿着鼓槌,敲打着膝上一个东西,黑色、圆形,音乐就是从那里发出的;女人站在他的前面,看着手机,指点着他击打的错点。
是一种打击乐器。圆盘上有15个音,不复杂,打起来应该比木琴和扬琴要容易些。不过,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便问道:这是什么乐器?
女人告诉我:梵音鼓。
这名字和它发出的声音很吻合,两者都能让人想起寺庙中香火的袅袅缭绕和经幡的缓缓飘动。
我又问: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一种合金。男人告诉我。
我又问他:多少钱一个?
他笑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别人送的。
在天坛,能见到很多新鲜的人事物。尤其对于我这样见少识稀又有些好奇的人。天坛是一本大书,翻开哪一页,都会让你开卷受益。
我听他打完一支曲子。女人拿着手机让男人看,指出哪里的节奏有误。我问:这是什么曲子,这么好听?她把手机递给我看,屏幕上现出了曲谱。是简谱,上面有曲名《大鱼》两字,原来是动画片《大鱼海棠》里的插曲。
男人收拾起他的梵音鼓,一边把它装进一个黑色的圆包里,一边对我说:这玩意儿能让我烦躁的时候静下心来。还能治抑郁症!
女人不动声色地对我启蒙:所以,它又叫无忧鼓。
男的站起身来,背起梵音鼓,对我说了句:回家再打它去喽!
我对他说:这里打它比在家要好!
他微微地笑了:那是!这里清静,古树又多,郁郁葱葱的,适合这玩意儿!
什么东西都需要相适配,剑鞘、鞍马、古松柏和梵音鼓,还有这一对男女。望着消失在古柏树荫中的这一对男女,我这样想。
藤萝架下:红风衣女人
来到我最熟悉的藤萝架下,满架花叶凋零,却远远看见人影幢幢,各色衣裙闪动,如蝴蝶翻飞,还能听到胡琴声和唱京戏咿咿呀呀的声音。是这里常见的情景,常听到的声音。不用说,是北京人在这里自娱自乐,一般外地人很少到这里来,偶尔路过,只是照照相而已。
我走进藤萝架,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拉胡琴的男人和一个唱戏的女人,都有60多岁的样子,男的坐在藤萝架下的长椅上,身穿一件夹克衫,女的站着,身着一件鲜红的长款风衣,正唱《霸王别姬》。围观者大多是女人,穿得都跟要参加比赛似的花枝招展,听着、说着、笑着、叫好着。
我坐在他们对面,画拉琴者和唱戏者。一段唱毕,唱戏的女人走到我身前,好奇地看我画的她,说我把她画得太年轻漂亮了。我笑着说她:您本来就漂亮嘛!她确实长得不错,身材高挑而清瘦,束腰的红风衣把她勾勒得更显亭亭玉立。她听了我的恭维,一摆手说:还漂亮呢,都老眉咔嚓眼了!我说:您才多大呀,就老眉咔嚓眼了?没等她答话,旁边一位胖胖的女人说了:67了,属马的,我们都是属马的!我指着他们这群人开玩笑说:你们这是万马奔腾呀!他们都开心地呵呵笑了起来。
聊起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同学,自疫情以来,彼此都没见过面,这是第一次聚在一起,听风衣女人唱戏,顺便聚聚会。这是在天坛常见的事情,一般都是居住附近的同学聚会。我以为他们也是这样,一问,原来他们家住朝阳、海淀,都离天坛不近。专程到天坛,是风衣女人的主意,说在天坛唱戏的票友多,没准儿能碰上,可以相互切磋切磋。
我问风衣女人:您唱得不错,挺有梅派的味儿,什么时候开始学戏的呀?她一听很兴奋,告诉我去年才学的。我连忙夸赞:才学一年多,就唱成这样,您可真了不得!她说:去年不是来疫情了吗?宅在家里出不去,就天天跟着录音学,给自己找点儿活干!我说:您这活可干得真不赖!可不是每个人学一年就能唱成这样的!
旁边那个胖胖的女人,指着她对我说:她当过我们班的文艺委员,上学时候就能唱会跳。我们全班同学,就她一人上了大学!她笑着谦虚地说:是工农兵大学。问她学的什么,她说是体育,大学毕业后在中学里当体育老师,一直干到退休,一辈子,眨巴眼儿,就快过完了!
聊完了,也画完了,我站起身,转身要走,胖胖的女人拦住了我,指着她对我说:她还想给您跳段新疆舞。看她已经脱下风衣,里面穿着红色的毛线衣,里外一身红,正拿录音机,找到伴奏的舞曲,走到藤萝架中间最宽敞的地方,跳了起来。一看,就知道跳过不知多少遍,很娴熟,也很自得投入。一曲舞罢,她对我说:我再给您跳段蒙古舞吧。说着,在录音机里找到伴奏的舞曲,是熟悉的《鸿雁》,随着优美的音乐,她跳得很尽情尽兴,我鼓起掌,她的那些同学也鼓起掌来,路过这里的游客也鼓起掌来。也许作为旁观者,我只是看个热闹,但是,在这两曲舞中,风衣女和她的同学经历了从青春到晚年漫长的人生岁月,叠印着他们相互的流年碎影,以及花开和梦碎的声音。
难得的一次同学聚会。风衣女人,没有埋怨我贸然闯入,相反把我有些漫不经心的夸赞,当作知音看待,让我惭愧,也让我感动。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一点点的信任和知音,会让彼此的心靠近一些,这是人们内心需要的,也是难得的,哪怕只是短暂如风的瞬间。
西天门里:轮椅上的老爷子
午后初冬的暖阳下,我坐在西天门里的甬道北侧。我爱坐在这里画画,对面浓郁的树荫中,隐隐约约能看到斋宫的外墙,再远处,还有三座门影影绰绰,景色不错。更何况,甬道直通祈年殿前的丹陛桥,来来往往的各色游人很多,衣着鲜丽,适宜入画。
身边来了一位坐轮椅的老爷子,是位中年妇女推他过来的。老爷子好奇地看我画画,和我聊了起来。那女人对老爷子说了句:您先在这儿聊,我去那边,待会儿回来。说罢,转身沿着后面的一条小路走去,不远处,有个白色的藤萝架,里面有人头攒动。
老爷子指着女人的背影对我说:我闺女,每一次来,把我放在这儿,她都上那边去,那儿有熟人,有话说。然后,他笑了笑,又说:整天伺候我一个老头子,她说话,我腻烦;我说话,她不爱听,嫌我啰嗦。树老根多,人老话可不就多呗!
老爷子爱说话,我乐意听,他显得很兴奋,碰见了知音,对我说:你说,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闺女姑爷都不爱跟我说话,来到天坛,人倒是多,谁也不认识,更没法说话,还不让人憋死?
我对他说:您敞开说,我爱听!
不耽误你画画呀?
画画本来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不碍事的!
老爷子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也听明白了他大半生的轨迹:今年79岁,小时候,家住房山农村,上世纪60年代入伍当兵,因为射击打浮靶是全师独一份的优秀,立了三等功,破格入党提干。复员到北京城里商业系统一家单位当党支部书记,管着下面好多家副食品商店。后来,超市发达,副食品商店纷纷倒闭,人员下岗的下岗,转行的转行,买断的买断。他是老资格,被调到公司的工会,是闲差,干了没几年退休,每月拿五千多元的工资。退休没多久,老伴得病去世,前几年,他过马路被一辆小汽车撞折了腰,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了。
我对老爷子说:您够倒霉的!
老爷子摆摆手说:倒霉的不是我,是我这闺女!他冲藤萝架指了指。
老爷子有三个闺女,这是大闺女,今年51岁。二闺女和三闺女,比她小十来岁,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都比她好,后来都考上了大学,结婚之后的日子都比她强。
我们这个老大,不好好学习不说,还早早就搞上了对象。搞对象也不说,非得搞个外地的;搞个外地的也不说,还没有工作。你说让人头疼不?没办法,我豁出老脸找人说什么也得给姑爷安排个工作呀。可你不知道,我已经豁出一回老脸,求人家给我这个大闺女安排一回工作了呀!你说我的这脸得有多大吧!幸亏人家觉得我资格老,给我面子,把他又安排在副食店工作了。谁想到呢,副食店不景气,两口子早早买断下岗,每月那点儿工资,都不够交房租的。这不,他们的孩子要结婚,没房子住。他们两口子把房子给孩子结婚用,跑到我这儿住来了,说是可以照顾我。倒也是,每天推我到天坛来转一圈。
我问老爷子:您那两闺女呢?
那两闺女,每月来家看我一次,每次给我一千块钱。我瞒着她们两人,把这钱都给了大闺女了,每月再从我的工资里拿出两千也给她。老闺女后来知道了,我以为她会不高兴。谁想她只是对我说了句好肉不疼赖肉疼。可你说怎么办呢?我在,每月还有五千的退休金,我要是一走,你说他们两口子可怎么活呀!让他们存点儿是点儿呗。好肉用不着疼,自有人稀罕,疼的可不就是赖肉呗。
说着话,大闺女回来了,对老爷子说了句:今儿说痛快了吧?不早了,咱回家吧!还得给您做饭呢!
她推着老爷子走了。轮椅消失在蒙蒙的树荫中。树上已经有不少叶子变黄了,灿烂的阳光下,像打碎的金子,散落在枝桠上闪着光,有些刺眼。
双方亭:晒太阳的教授
中午时分,双环亭和双方亭下,是北京老人的天下。特别是冬天,这里暖阳高照,视野开阔,不少老人都会坐在亭子走廊里的长条椅子上,老猫一样,懒洋洋地晒太阳、吃东西、冲盹儿,或眯缝着眼睛想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在心里暗暗骂骂那些恨得直咬牙根儿的恶人。
那天,双方亭中,有个女人坐在那里织毛衣,逆光中,看不清她的面容,但她清秀的剪影,和亭子雕梁画栋的鲜艳色彩相得益彰。我坐在离她很远的长廊这一边,画她的剪影,看见一个男人闯进了我的画面,弯腰在和她交谈着什么。没过一会儿,这个男人走下双方亭,背着手走到我的身边,弯腰看了看我的画,连声夸奖:一看就知道你画得不错,练过素描……还没等我谦虚几句,说我根本没练过什么素描,他不容分说,紧接着又对我说:我也喜欢这个,不过,不是画画,是书法!
我赶忙夸他:那您厉害呀!
说着话,走廊这边走下来一个高个儿的男人。他指着这个高个儿男人说:人家才厉害呢,他是教授!
一起聊起天来,知道他们都常到这里来晒太阳,渐渐熟了起来。他家住沙子口,教授住宋家庄,离天坛都不算远。他弓着腰,笑呵呵地说:到这儿晒太阳,比在哪儿都强!然后,他问我多大了?我让他猜,他说:反正没我大。我问他多大了,他说67。教授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这时候插上话,对我说:看你没我大。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他1950年出生的。我说:我1947年的……
我们三个小老头儿,在这冬日的暖阳下,比谁的年龄大,像小时候比赛撒尿谁尿得远似的,还充满儿时的天真。
67岁的男人走了,教授忽然老眼尖锐地问我:你是学文科的吧?
我点点头。
他接着说:我是学工科的,学的锻压。然后又问我:你哪所大学毕业的?
我告诉他中央戏剧学院。没等我再说话,他紧接着说起自己,好像刚才没有说话的机会,憋得他要一吐为快:我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在石家庄工业学院教书。这才容得我问他:你毕业后就到石家庄了?他摆摆手:没有,先到了三线工厂搞设计……
说到这里,他忽然停顿了一下,然后,转移了话题:教授,就是说着名声好听,没什么用。人哪,不能总调动工作,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才好,像我的一个同学,一直在上海搞设计,现在年薪三十万。我的另一个同学,和我一样退休了,现在还在原单位搞设计,不算退休金,每月还能拿一万五。
我劝他:也别这么说,心情好,身体好,比挣钱多管用!
他说:那是!我在课堂上讲起课来,就忘记了年龄,忘记一切,心情就特别好。
我们两人一直坐在走廊上的长椅上说话,面对着面,他快人快语,说话跳跃性很大,大概一生经历的起起伏伏,在心里瞬间如水流撞击得波涛翻涌,忽然让他有些为自己的人生感慨。
突然,他说自己是学俄语的,问我学什么的。我告诉他学的是英语。话音刚落,见他旋风一般蓦地站了起去,黑铁塔一样立在我的面前,立刻脱口而出,高声朗读了很长一阵子俄语。声音高亢有力,浑厚响亮,像是平地炸雷一般,吓了我一跳。他没有看我,也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眼睛注视在前面,长廊外一片树木绿荫蒙蒙。他充满激情,一气呵成,回音在午后静静的长廊里回荡着。
朗诵结束,他告诉我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然后,他强调补充说了句:马克西姆维奇·高尔基。

